星期一早上七点半,火车从D城准时发车。这列火车只有两节卧铺车厢,工兵团已经提前给顾铭、郑才学、向阳三人安排好了铺位。随行有一位姓祝的工程师,他在铁路沿线各个驻点总共干了二十三年,向有勇退休前一年把他调回机关。谁知这人倔得很,逢人就说机关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玩文字游戏,编一些连自己也不信的鬼话,背后没少对人发牢骚。弄得向有勇哭笑不得。等到魏君鼒履新,又把他下放到基层。这次他恰好坐这趟车返回驻点,单位便安排他给顾铭当向导。
D城有个不成文的说法:虽然大家都是兄弟部队,但因为工作分工和性质不同,自然也要区分三六九等。习惯上,雷达、遥测、光测、通信、发射等与试验任务关系密切的单位被尊称为“一线”,后勤单位与勤务保障单位则被纳入“二线”。工兵团是典型的“二线”单位。工兵团这条铁路与D城同龄,横亘在戈壁滩上已经有半个世纪。我国发射的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卫星、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艘试验飞船等等,都是由这条铁路运送到发射场。
列车运行会造成钢轨变形,存在安全隐患。在铁路沿线驻守的部队,主要承担巡道工作和铁路日常维护。另外专门有人负责对钢轨作探伤检查,更换有损伤的铁轨。这是一门技术活。祝工程师接手这项工作以后,带着三个战士,背上干粮和水,推着超声波钢轨探伤车,一毫米一毫米向前推进。他们一天大概只能检测十公里,晚上一般就近宿在沿线的驻点。现场工作中,不确定因素很多,错过饭点是常态,甚至有时候不得不在戈壁滩上露宿。还有,天气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经常遭遇沙尘暴。沙尘暴有时候非常吓人,戈壁滩上又没有遮挡,刮得人都站不稳。有一次,一个巡道的战士被沙尘暴卷走了,最后在三十五公里之外,被一名当地群众救起。现在一说到这事,那个小伙子仍然惊魂未定,有点劫后余生的意味。好在祝工程师沿着这条铁路走了二十多年,还没有被卷走过。粗略计算,这些年他大概走了有四万两千多公里。他完成了三个半红军长征,这是他一辈子的荣耀。他说。
“你一定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啰?”顾铭低着头,在笔记上飞快地记录。
“说不上。”他不停搓着双手。
“不喜欢怎么能在一个岗位上干这么久?”
“咋说呢?”他搓搓衣角——上面有点油渍,沾了沙尘,脏兮兮的。“打个比方吧!我老婆是我们老家的,我俩是别人搓合的。结婚以后,差不多有十年,一直都是两地分居,一年到头,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一两个月。我在点号工作,她随军以后,我没有两地分居假,在一起的时间好像比原来还短。路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部队和一群光棍们待习惯了,老爷们心里敞亮,不像女同志,小肚鸡肠,啥事都计较,有事没事就拿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斗嘴,我听着就来气。孩子又小,不是哭就是闹,我又不会哄,烦得够呛,还不如周末待在连队,和战士们打打牌呢。嘿嘿嘿……你看,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结婚二十年了,从来没有对老婆说过一次‘我爱你’,说不出口!对我老婆,我说不上喜欢。如果上天给你一个机会,你愿意重新选择一个老婆吗?有的男人可能愿意,但我不愿意,而且也没往这方面想过。说不定娶个年轻老婆,还不如现在过得自在呢。那工作呢?我想,工作也是这个道理,你换一个工作,就一定比现在好吗?”
他摸摸上衣口袋,又摸摸裤子口袋,摸出一盒七块钱一包的红兰州烟,把烟盒倒过来,在手心磕了两下,几枝香烟的黄色滤嘴从烟盒里探出了头,他抽出一枝送到嘴边,叼上,又把烟盒送到顾铭面前,“首长,来一根!烟不好,嘿嘿——”顾铭说不要,他又递给郑才学。郑才学抽出一枝叼上。又送到向阳面前,向阳摆手不要,他就把烟收起来了。郑才学掏出打火机,自己点着,又给他点上。他吧嗒嗒抽了几口。“其实,我们上一任团长也跟我谈过话,要调我回来。我没同意,谁知道他就直接把我调回来了。你说这人——”——他抽烟的频率明显加快——“再大的领导,你也不能这么干吧?”
“领导也是为你考虑。”顾铭说,“这工作不容易干!年龄大了,换个清闲地方养老,也是对的。”
“为我考虑就应该尊重我的意见!驴不喝水还能强按头?”他瞪大了眼睛,黑黝黝的脸变成了黑红色。嗓门也一下子提高了,把顾铭和郑才学等人吓了一跳。“我是他接过来的兵,多少年的关系了!他对别人可以滥用职权,对我就不行!你们知道吗?我在机关工作了一个多月,回家跟老婆干了好几架。这还不都是因为他?这个老向,让我怎么说呢?不过,老向这人能力水平不见有多强,但有一样好处——不贪!”
向阳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他没有见过祝工程师,估计他也没有见过向阳,否则,他应该不会当着儿子的面说父亲的不是。工程师讲这番话时,顾铭手托着下巴,脸上毫无表情,显得非常严肃,郑才学却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时不时看向阳几眼,似乎想笑,却忍住了没有笑出声。向阳觉得他还不如笑出来,这种忍俊不禁的样子更象是种侮辱。假如父亲听到这番话,不知将作何感想?想到这里,向阳不由一阵悲哀。他记得父亲退休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在工兵团三十年,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为基层办了一些实事,尤其是大大改善了铁路沿线部队的住户和饮用水,解决了部分官兵的两地分居困难。从父亲的立场来说,他肯定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是,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说你好。其实,不光是父亲,包括任何一个人,都别想赢得所有人的赞美。甚至有时候,赢得一个人的赞美都是那么困难——尽管你觉得已为他倾其所有,可是,他并不领情。因为你辛勤付出换来的,也许并不是他所需要的,它在他眼里的价值等于零。更何况,父亲这个人一向刚愎自用,从来都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他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地进行赏赐,这些东西,本身又有多大意义和价值?
车到了第一个驻点,他们下车了。驻点一个干部带着两个战士,推着三轮车,把他们的随身行李装上,带着他们前往驻点。从硬座车厢下来两个穿军装的年轻小伙子——这是工程师三人团队中的另外两个人,工程师安排他们去拿探测装备。他与顾铭一行简单告别后,马不停蹄,带领团队整装出发了。
这个驻点有个大院子,七八间营房,中间是半个篮球场。院子周围稀稀落落地栽了几颗树,院子后面是一块菜地。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少尉,带着三个士官和三个义务兵。一日生活很简单,早上起床,一个士官带着一个义务兵准备早饭,其余几个人或队列训练,或绕着院子小跑几圈,然后回去洗漱、吃早饭。吃完早饭休息半小时,一个士官带着一个义务兵去巡道,沿着铁路一直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检查铁轨是否有故障,顺便把散落在铁轨中间和枕木的石头、垃圾清理干净。一直走到下一个驻点,跨过铁路,沿着铁轨另一边原路返回。一来一去大概需要三个小时。回来恰好赶上吃中午饭。没有巡道的几个战士,由军官带着去菜地干活,种一些常吃且易于生长的蔬菜,比如辣椒、茄子、西红杮、小白菜。夏秋季节,这些菜都吃不完,可到了冬天,驻点战士的餐盘里很难见到绿色。火车从D城带过来的,主要是主食、调料和一些肉类,蔬菜很少。大多数驻点陆续配了冰箱,但仍有一些驻点没有冰箱,肉类和菜蔬都是自然存放,偶尔变质是免不了的。好在驻点的战士大多数都是些农村兵,家境不见得好,大鱼大肉供着已经谢天谢地了,何况肉食还没有腐败得难以下咽,不至于吃坏肚子。
今天的小炒肉明显不够新鲜,厨师又是自学成才,一抬手,半瓶酱油差点倒个底朝天。他又信奉好厨子一把盐的黑暗料理哲学,谁知他个头不高,但手掌奇大,一只手轻松抓一只篮球。他也知道自己手大,把盐抓在手里,又抖了抖,细小的盐粒像漫天飞雪一样从指缝滑落,他这才把剩下的盐撒进锅里。可这道菜的含盐量已经严重超标了,用土话说,打死卖盐的了。这些战士们习惯了厨子的重口味,倒不以为然,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郑才学端起菜送到嘴边,咧着嘴,一副嫌弃的表情,到底还是吃了。顾铭眉头紧锁,忽然问双手放在膝盖上、迟迟没有动筷子的厨师:“小伙子是山东人吧?”
小伙子坐直身子,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兴奋得脸都红了,说:“首长,你——咋知道的?俺济宁的!”
“吃出来了。”顾铭冷冷地说。
这一顿饭吃得不愉快。大家都看出来了,厨子也看出来了,他知道首长这时候一定惜字如金,“表扬”已经不是暂时迟到,而是永久缺席了。他战战兢兢地坐了一会儿,也不敢动筷子,刚好少尉吃完了饭,他赶紧端着碗进厨房盛饭去了。盛完饭,又去端了一盆西红杮鸡蛋汤,然后就回到厨房,再也没有露脸。
吃完饭,少尉带着顾铭等人先参观了战士宿舍。宿舍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很简陋,水泥地面凸凹不平。里面摆了四张高低床,被子都是标准的“豆腐块”,三张下铺床上的被子已经洗得发白了,一看就知道是三个士官的。床底下,刷牙缸子、军用皮鞋、迷彩鞋、拖鞋一字排开,摆得整整齐齐。牙刷头朝上,靠着牙缸右侧,牙膏则靠向左侧。从宿舍出来,少尉又带着他们去菜地。菜地有一亩大,几个战士撸起袖子在那里干活。顾铭背着手走过去,他们都放下工具,立正站立,异口同声地喊“首长好!”顾铭摆摆手,颔首微笑。
也没有什么可转的地方。顾铭提议到下一个驻点去。可是没有车,少尉就安排一个士官骑着三轮车,载上行李,让顾铭坐在行李上,郑才学和向阳跟在后面。士官骑得很慢,向阳勉强还能跟得上,郑才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水把迷彩服都溻湿了,裤腰带也跑松了,浮在肚脐眼上一上一下。
“他妈的!我们这是要去飞夺沪定桥呀!”他说。
顾铭忍不住,笑着说:“老弟,你别把裤子跑掉了。”
“不怕!”郑才学喘吁吁地说,“在戈壁滩上裸奔不违法。我的这一副家伙什儿兄弟们都齐全,没人稀罕!是不是,班长?”
骑三轮车的士官回头笑笑,没有吭声。
下一个驻点与这个驻点并无两样,六七个人,三五间房,一两亩地。当然也有不同,这个驻点连三轮车也没有。顾铭看了大摇其头。驻守的战士介绍说,他们这儿算是条件不错了。下一个驻点只有一名战士,是个三级士官,他的妻子带着孩子长期陪他住在这里。顾铭听了,坚决要求到下一个驻点。那个战士只好推上三轮车继续赶路。
两个驻点之间没有公路,战士推着三轮车,沿着铁路一步一步往前走。下午三四点钟,烈日如火,炙烤着铁轨和沙地。茫茫的戈壁滩上没有树,甚至也没有草,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土黄色骆驼刺。脚踩在沙地上,连鞋都要被融化了,裸露在外的皮肤被晒得生疼。几个人都是大汗淋漓,彼此交流着绝望的眼神,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驻点。这个驻点只有三四间屋子,屋前有几棵树,都被一圈矮矮的砖墙围在里面。有两棵树中间扯着一根细铁丝,铁丝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其中一棵树的树干上挂满了玉米,地上有晾晒的辣椒、豆角、茄子。一个晒得黑乎乎的小孩,上身只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短袖,光着屁股满院子乱跑,他高声阔气地叫喊着,为自己踉跄的步子助威,鸡嘴似的小鸡鸡轻轻晃动着。此情此景,看上去更像是一户农家,而非军营。
这名军嫂才二十出头,穿得花里胡哨,两个脸蛋红彤彤的。一见来了生人,连额头也变成红色了。士官穿了一条迷彩裤,上身套着一件黑色T恤。他抬手准备敬礼,大概是觉得自己穿着便装,有点不合适,又把手放下,双手不停地揉搓裤缝,手指尖微微抖动。
军嫂准备的晚饭也很简单,洋芋糊糊面,一碟拌黄瓜,一碟拌洋葱。她有点不好意思,解释说是这个驻点小,每周三火车才会送一点菜。碗也只有四个,顾铭他们四个人吃,士官坐在旁边看。大家都饿了,一人吃了两碗面条。军嫂刚给这个盛好,那个又吃完了。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也跟着跑,不小心绊倒了,哇哇大哭。她抱着哄了一会儿,还是哭。军嫂气得用一只胳膊把他夹在腋下,照着光屁股蛋子狠狠打了几巴掌,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军嫂抱歉地笑笑,抱着孩子出去了。
顾铭不知道这儿只有四个碗,一边往嘴里扒拉面条,一边说:“小伙子,你也吃呀!别跟我们客气!”
士官红着脸说:“首长,你先吃。等你们吃完我再吃。”
吃完饭,送他们的士官推着三轮车回去了。顾铭问起这名士官工作和家庭的一些情况。他嘿嘿笑了,放下碗,来回不停地搓动双手。
“说啥呢?我就是一个普通战士,一天到晚也就在铁路上蹓弯,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说。
“介绍一些你自己的情况。你爱人什么时候来部队的?”顾铭问。
“快两年了。”他说,接着陷入沉思,足足有两三分钟,这才抬起头,坐直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收敛笑容,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
“报告首长,我叫王宏业,男,甘肃庆阳人,现年二十九岁……”
他慢慢打开了话匣子。他守护这条铁路已经整整十年了。之前,他们这个驻点有三个人,四年前,有两名战士换到别的驻点去了,这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养了一条狗。早上,他煮上两包方便面,再加两根火腿肠。给自己盛一碗,再给狗盛一碗。吃完饭,收拾停当,他就背上工具包,扛上铁锹,带着狗一起巡道。顾铭要看他的工具包。他出去拎进来,里面是铁锤、扳手、道钉。他解释说,这些东西是维修铁路用的,之所以扛着铁锹,是清理风刮到铁轨上的沙子。
他背着工具,带着狗沿着铁路一直往前走,直到碰上下一个驻点巡道的战士,双方交换巡道牌,他再沿着原路返回。中午就搞上两个菜:一荤一素。把米饭和菜拌在一起,他一碗,狗一碗。无聊的时候,就跟狗说说话。狗一听到他说话,就端端正正地蹲在他面前,时不时汪汪叫上两声,好像能听懂他的话。一个人,一条狗,相依为命,倒也不嫌寂寞。
可是,有一天他午睡醒来,发现狗不见了。他慌了,每年都有新兵蛋子吃不了苦,想各种办法当逃兵,有假装喝农药的——其实喝的是洗衣粉水,有装病的,有信佛教的,还有人晚上偷偷往外跑,但戈壁滩那么大,又没有路,黑咕隆咚哪里是尽头?人都跑不出去,狗又能比人聪明到哪儿去?他沿着铁路往下一个驻点走,走出十几公里,没有找到狗,只好回来。天黑了,院子里空荡荡的,连个鬼影也没有,他的心里也空荡荡的。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夜静得一丝声响都没有,他的心里有点发毛,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捱到第二天,早饭也没有吃,就出发去巡道。巡道结束,他又沿着铁路,朝另一个方向出发,去找他的狗。天天如此,整整找了半个月,连一根狗毛都没有找见。
“这个死狗,竟然比人还耐不住寂寞!”他苦笑了一声。
大概半个月后,三十多公里外的另一个驻点的战士,巡道结束返回,一路拣石头玩,拣到了几块沙漠玫瑰石,很漂亮,他就离开铁路,一直往前面的山跟前走,希望能有意外的收获。他在离山不远的地方发现了那条狗,它已经死了。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一只鸟都飞不出去,更何况是一条狗?
后来,团领导大概也是考虑到,像他驻守的这种单兵驻点,生活很不方便,决定组建夫妻维护点。他跟妻子商量,她竟然愿意过来,于是就迅速办理手续。一个多月后,妻子拎着大包小包,背着一岁多的孩子就来了。她来了以后,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妻子从老家带过来一些蔬菜种子,两个人就在院子后面开发出一小片菜地,种上了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豆角、卷心菜。蔬菜成熟的季节,他们一家人吃不完,巡道的时候还给别的驻点也带一些。
孩子闹了一会儿,睡着了。军嫂把他放在另一个屋里,进来收拾碗筷。顾铭问她在这里是否习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她说:“习惯是习惯,在老家也是种地。就是孩子一天比一天大,在老家,人家都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了。可在这里我往哪儿送呀?也没有小孩子陪孩子玩,他都快三岁了,除了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话都不会说。我想——”——她憨憨一笑,看了一眼端端正正坐在一旁的丈夫——“我想带孩子回老家上学。可是,我们娘俩一走,把孩子他爸一个人留在这儿,谁给他做饭吃呀?衣服脏了谁给洗呀?嘴闲了谁跟他谝闲传?他又不吃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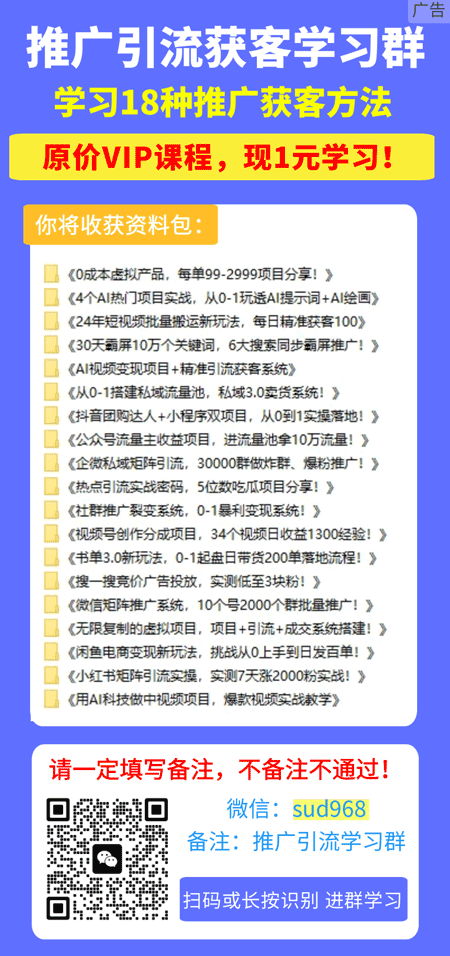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iheng8.com/31882.html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