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恋街。这印象打我记事时起。父亲说,母亲她爹是个货郎,母亲身上有她爹遗传的基因。摇着货铃,走村串巷,好不快活。母亲却说,她爹面向的是离街最偏远的地方。农闲时节,大清早出门,满满的一担,这个村那个湾,一天要走烂一双草鞋。没钱的人家用米豆来换,回来时是更沉的一担。那是没人干的苦力活,哪来的快活!
长大后,我渐渐晓得,母亲恋街,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无奈。
那些年,我家的后菜园,每年都要栽种两茬大片的春菜(雪里蕻),当春菜长得密密匝匝,郁郁葱葱,高过膝盖,叶面泛着油亮的红晕,嫩得能掐出水来的时候,母亲就瞄准几个好晴日,把它们齐根砍掉,然后抱到家门前的池塘里清洗,再把一棵棵硕大的春菜倒挂在两树间牵扯的绳索上、后园的篱笆上、树杈上,及搭好的帘子上。每年的这时候,我家就被这丰收的春菜包围着,成了一道风景。
在风火日头里,春菜两三天就风干了水分,一棵棵变得瘦小软绵,一场剁腌菜的苦重活儿就由母亲领衔开始。一家人轮换着,总能把腌菜剁得特细。
吃过母亲腌菜的人,都说母亲的手好,腌的菜从来不腐烂。其实,母亲的腌菜香、味道好,完全是母亲认真仔细的结果。
母亲将剁好的腌菜先撒上盐,再一把一把地将盐与腌菜揉匀,直到揉得腌菜现出湿润的水分,才一大捧一大捧地往早已洗净晾干的坛子里装,装入一些后就用杯口粗的木棍用力杵实,再装一些,再杵实,装杵到坛口时,坛口往往能溢出一些深绿浓酽的汁液。然后,母亲就把一团干净的稻草揉软,严严实实地密封在坛口上,再在房屋的一角铺上一层厚厚的灶灰(稻草灰),将坛子反扣在上面。每年母亲做的腌菜都要把家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坛子装满,家里的角落旮旯里都扣满了形状大小不一的腌菜坛子。
母亲做的腌菜需要三五个月时间的等待,直到确信腌菜彻底腌熟了,母亲才会翻坛开盖。这时的腌菜泛着一层微黄,溢出一股清香,不用下锅,用手拈上一点放入口中,就让人有一种奇味绵长的快感。
余下来,就是母亲旷日持久地挑着腌菜去集市卖。那时的永安堡集市是个露天早市,父亲说是个“强偷街”,意思是每天一大早只有两三个小时开市。为抢个好地点,母亲往往要在鸡叫头遍就出发,往往在太阳升起时就能卖完两竹篮的腌菜,正好回家赶上生产队的出工。
那几年,大哥因受“成分”的牵累,眼瞅着快成大龄青年时才好不容易说上一个媳妇。为了彩礼钱,母亲又把家门前靠塘塍的一块空地打埂围上,种上春菜。于是,母亲上集市卖腌菜的负担就更重了。直到如今,隔壁的堂兄还常常开玩笑地说,大嫂是用腌菜换来的,是个“腌菜媳妇”。
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农民出工随意自由。永安堡的集市也由“强偷街”变成了半日街,母亲留守集市的时间也长多了,大多日回家时已是日头快当顶了,往往担着的空筐里总会有一些什么油条面窝发糕的,美得我们姊妹都夸母亲好。但父亲却总爱说教说教,嫌母亲上街的时间太长,耽误了地里的活儿。
那些年,我家承包了十多亩良田,还有家门前的大池塘,家中的厢房也养上了一头一年能下两窝崽的黑母猪,虽然经济上改善了许多,但人却更忙,更有奔头了。父亲是种田的好把式,耕种管理收割样样在行,粮食丰收得装满了粮仓,留足口粮后,每年都能卖出去好多些。但那时家家都不愁吃,粳米不值钱,母亲天天在街上,知道市场的行情,就撺掇父亲种糯稻。
那个时候,我正与妻相处,自然给父母又增添了经济的担子,但此时父母却并没有卖腌菜时的窘迫感,而是整日乐呵呵的,似乎心中蛮有底气,有更好的盘算。待糯稻丰收后,家中的箩筐、簸箕、筛子就伴着父母忙开了,一袋袋精心整理好的糯米晶莹油亮,如珍珠一般。从不敢上街的父亲也胆大起来,帮母亲把一担一担的糯米送到街上,于是集市上又多了母亲一担一担叫卖的糯米。我的妻也自然被堂兄叫成了“糯米媳妇”。
常言说:树大分叉,儿大分家。随着“腌菜媳妇”在永安堡街道建上新房,和“糯米媳妇”进城安家,父母把持几十年的一个十多口人的大家,就只剩小妹与小弟还在父母膝下。这时的父母,年岁渐高,对付庄稼的体力日渐衰弱,就把农田的双季稻改种成一季稻。由于政府配发的种子优良,产量也少不了多少,但人却轻松了不少。父母一生勤劳惯了,这省下来的庄稼活就转变成对鱼塘的精心管理和对猪的喂养呵护。于是,那些年母亲的集市就又多了猪娃哼哼嗷嗷的叫声和比猪娃还要肥胖的草鱼、鲤鱼、鲢鱼等的拍打蹦跳,每年的收入供开销后,还有结余存上银行。
母亲虽说是妇道人家,但眼光一点也不比男人差。母亲就用这宽松的经济,一门心思地鼓励小弟发奋求学,最终小弟争气,考取了个一类重点大学。父母用鱼钱猪钱供小弟上完了大学。小弟毕业后安家都市,娶了个白领媳妇。堂兄风趣地说,咱老李家咸鱼翻身,土猪成象,鱼养的学生猪供的学生,娶回个“洋媳妇”!
父母终身务农,泥里水里冻伤了腿、累伤了腰,六十多岁了,繁重的农活实在干不了了,才搬到我这小城上寄居在儿子这里。劳作一生,本应该休息,但不及几天,便坐卧不得安宁。父亲颇有雄心壮志地说:“共产党这好的政策,你妈又是个生意精,不做点小生意那是糟蹋了!”
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便不分东西、不论黑白,什么小生意都做,卖小菜、卖甘蔗、卖水果,后直到卖咸菜才在家门右侧的小临时菜市场定下位来。这咸菜大多是父母在时令季节豆角、萝卜、雪里蕻、大椒等便宜时买下的,经过自己精心加工腌制而成。
父母卖咸菜形成了自然的分工。父亲在家负责清洗切碎配料,母亲负责在集市摊点叫卖。这样的分工似乎颠倒不得。在摊点叫卖时,母亲人善手松,每每称好后,还要再加一勺给人,自然回头客多。母亲除中午因买菜的顾客少,休息一会外,一天大多时间都浸泡在集市里。我们子女说她苦,而她却说,这里人来人往的,这熟人又多,有说不完的话,比在家里热闹多了,蛮快活的。母亲的咸菜生意一干就是十五年,以至人们忘记了她的名和姓,成了远近闻名的咸菜婆婆,我的家也被人指认上是“咸菜婆婆的屋”。
父母近八十岁时,思乡心切,执意要落叶归根。为满足父母的心愿,我们儿女在永安堡街上给父母买了一套房。房子就在二楼,一百多平方米,紧挨中心小学,下楼出门就是银行,过公路就是集贸市场,几十年前天天肩挑手提赶着上街的地方,如今真真切切地在躺着睡觉的床下。父亲爱溜达,广场、超市、银行、熟人的小店,每天都要遛一遍,累了就坐在家门前的邮政银行喝茶,他说他是银行的老客户,经理不嫌弃他,还欢迎他呢!
母亲则不同,依然流连集市,每天天一亮,就背着双手,步履稳重,慢慢吞吞地在集市上逛开了。过肉案、穿鱼摊、经果店、出菜圈,看时装、问稀样,饿了就在集市中的早点摊来一碗肉丝面,遇上个熟面孔就家长里短地拉扯开来。
我每次去父母那早了,就不见母亲,父亲风趣地说:“让街招魂去了!”我听了好笑地说:“过去那个穷街、‘强偷街’都是一天一个回合,现在这花花街、好吃街、好玩街、不打烊的街,去了还想早回来?”父亲说:“过去上街做点生意那像是去讨饭,现在逛街是看西洋镜,净找合口的好吃的,那没法比。”停顿一会,父亲又接着说:“你晓不晓得,你妈妈的名声大得很,这里的人都喊你妈妈是个‘逛街的婆婆’!”
是啊,母亲一生都爱上街,上街的名声确实大得很。由腌菜到糯米,由咸菜到猪鱼,由低头守摊到抬头逛街,由摸黑赶街到住在街上,由愁吃愁穿到在街上挑着吃选着穿。母亲的“上街”由苦变甜,由穷变富,由辛酸变快活。如今,新时代又把母亲的“上街”演变得一年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碧峰)
【编辑:侯方隅】
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武汉”客户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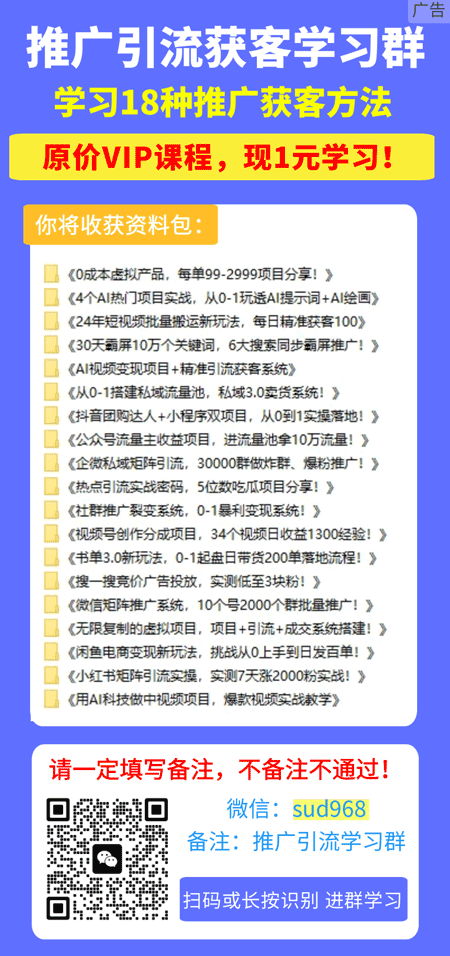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iheng8.com/100460.html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